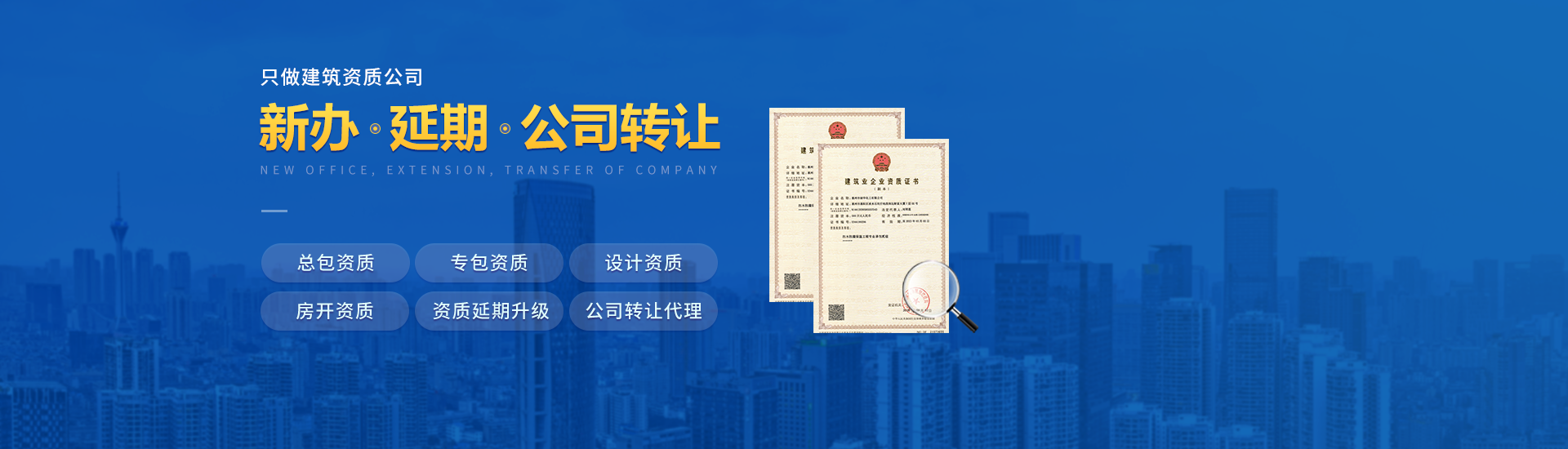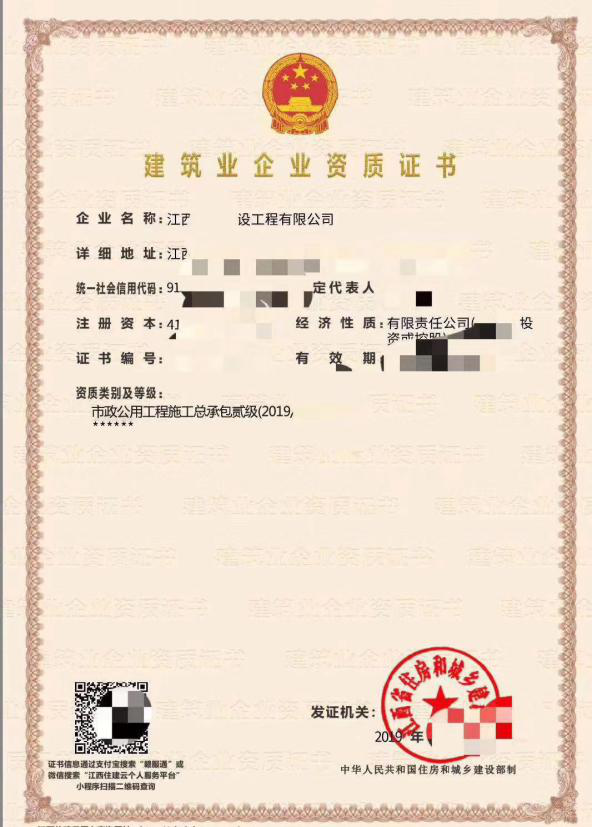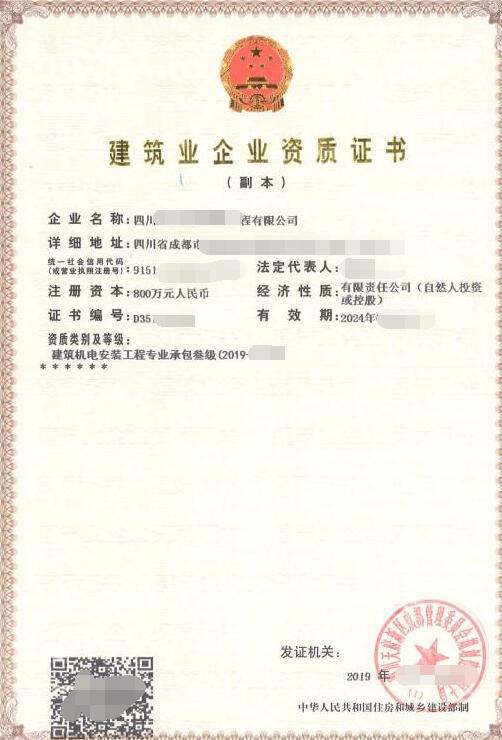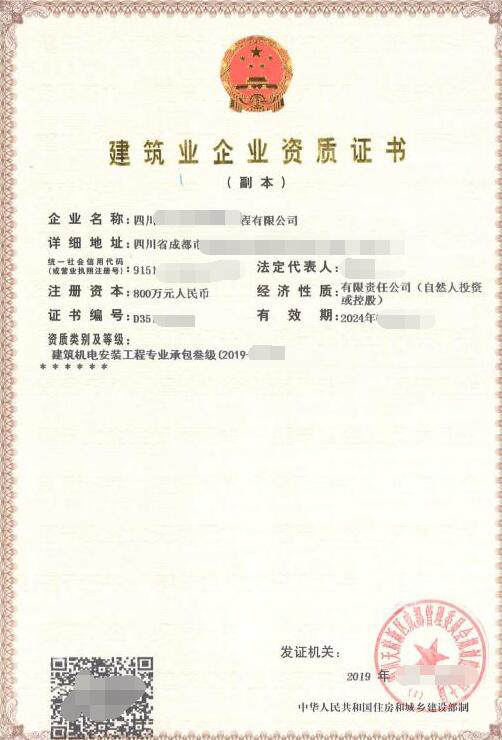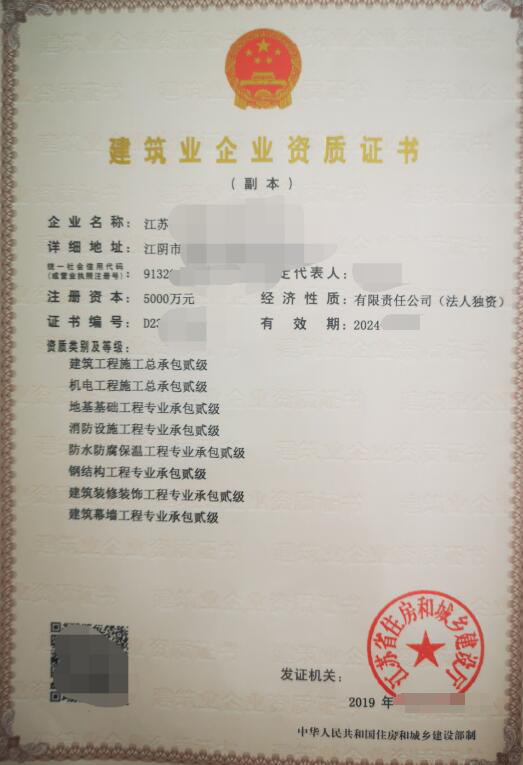1983年,廣州市南越王墓的驚世發(fā)現(xiàn),喚醒了嶺南一段塵封的遠(yuǎn)古記憶——從秦始皇揮師南征到趙佗“絕道立國”,從推行“和輯百越”的民族融合方略到實(shí)踐“同制京師”的宏圖壯志,這不僅僅是一份被時光完美封存的歷史提綱,更是一份來自祖先的珍貴饋贈。如今,它們以文物的形式展陳于南越王博物院,佇立于時光的渡口,仿佛能觸碰到2000年前的風(fēng),感受到時間的呼吸,如同聆聽一部娓娓道來的史詩。
南越王博物院合計(jì)建筑面積為4萬平方米,展示南越文王墓、南越宮苑、南漢王宮等考古遺址,承載著嶺南文化2000余年的歷史底蘊(yùn),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見證。
館墓合一——世界建筑精品
在廣州市越秀區(qū)解放北路上,一座紅砂巖建筑格外引人注目——這便是著名的南越王博物院。其前身可追溯至1988年建成的南越王博物館和2014年建成的南越王宮博物館。1983年6月,人們在越秀區(qū)解放北路施工時意外發(fā)現(xiàn)了南越國第二代國王——文王趙眜(趙胡)的墓葬。為保護(hù)這一珍貴遺址,發(fā)掘完成后,廣州市人民政府決定就地興建遺址博物館。
南越王博物館的設(shè)計(jì)重任,落在了已締造多座廣州經(jīng)典建筑的著名建筑大師——莫伯治先生肩上。作為世界公認(rèn)的中國當(dāng)代著名建筑師之一,他和他的作品被譽(yù)為“嶺南建筑之光”。
南越王博物館的設(shè)計(jì),面臨很多難題——墓室位于廣州繁華地段的小山丘上,四周高樓環(huán)伺,可用空間極其有限。在如此狹小的地塊內(nèi),既要原址保護(hù)墓室,又要興建展館陳列文物,更要彰顯其獨(dú)特價值,且無任何現(xiàn)成模式可循。
為此,莫伯治在深入研究后,廣泛借鑒中外古今紀(jì)念建筑的精華,尤其是從漢代石闕、埃及神廟闕門等造型中汲取靈感,由此開啟了建筑設(shè)計(jì)“新表現(xiàn)主義”的探索與嘗試——設(shè)計(jì)嚴(yán)格遵循《威尼斯憲章》原則,確保新建部分與歷史遺跡在形態(tài)上清晰可辨,真正做到“不以今損古,不以假亂真”。
古墓作為博物館整體布局的中心區(qū),其上方用鋼架結(jié)構(gòu)、金屬玻璃罩建造了防護(hù)性大棚,與墓室遺跡結(jié)構(gòu)有明顯的區(qū)分。考慮到墓主人與漢武帝處于同一時代,金屬玻璃蓋頂作覆斗形的幾何形體——這一造型直接呼應(yīng)了漢武帝茂陵的形制,同時巧妙隱喻了古墓原址上方的覆土封丘。
展館石闕和回廊、墓室護(hù)墻等部位采用了與原有墓室結(jié)構(gòu)材料類似的紅砂巖,可謂別出心裁。臨街的博物館正立面,用了1300多塊紅砂巖砌筑成石墻,當(dāng)中留出一線通道,作為展館大門的入口。左右兩堵石墻猶如兩座石闕,聳立在高臺階上。墻面上是由著名雕塑家潘鶴雕刻的兩幅巨型浮雕——高達(dá)8米的男女越人頭頂日月,赤足踏蛇,姿態(tài)威嚴(yán),象征驅(qū)逐邪惡,宛若守護(hù)門神,其下方左右分踞一對蓄勢欲躍的圓雕石虎。這些雕刻的原型均源于墓中出土文物——屏風(fēng)構(gòu)件、玉璧與錯金銘文虎節(jié),它們將典型的越、漢、楚文化意象,凝練地呈現(xiàn)于展館入口。
在古代,嶺南是越人的聚居地,刻在主體陳列樓東西兩面石墻的“越人善作舟”之作,則源自出土的銅提筒上的刻畫。這處細(xì)節(jié),不僅點(diǎn)明了嶺南先民的智慧,更直接呼應(yīng)了廣州作為中國南部海上交通樞紐的悠久歷史。觀眾在正式踏入展館大門前,便能觸摸到嶺南古文明的實(shí)體印記。
步入展館,一條44級的筆直蹬道迎面延伸,正對古墓核心區(qū)。這肅穆的通道,象征著古代帝王陵墓前的神圣神道。呼應(yīng)這一意象,大門外矗立的巨幅越人浮雕與蓄勢石虎,恰如神道兩側(cè)守護(hù)的石人石馬,昭示著墓主的尊崇地位。這一設(shè)計(jì),將嶺南這片古越人聚居地的歷史底蘊(yùn)與中原帝王禮制巧妙融合。
南越王博物館在回顧傳統(tǒng)的基礎(chǔ)上,以現(xiàn)代手法表現(xiàn)其紀(jì)念性和對2000多年前歷史文化的傳譯,既突出了歷史感又保持了地方色彩,成為嶺南現(xiàn)代建筑的輝煌代表。1999年,在國際建協(xié)第20屆世界建筑師大會上被評為“20世紀(jì)世界建筑精品”。
2021年9月8日,原西漢南越王博物館、南越王宮博物館合并組建成南越王博物院(西漢南越國史研究中心)。兩館合一,共同肩負(fù)起弘揚(yáng)嶺南文化的重任。
趙佗佐秦——嶺南納入中央王朝
作為20世紀(jì)80年代我國重大考古發(fā)現(xiàn)之一,南越王墓的發(fā)現(xiàn)不僅成就了一座獨(dú)一無二的博物院,也激活了嶺南大地的一段遠(yuǎn)古記憶。
“十四年屬邦工□蕺丞□□□”,這是一段穿越時空的銘文,它鑄刻在展廳內(nèi)青銅戈上,訴說著一個關(guān)于權(quán)力、制度與戰(zhàn)爭的故事,雖然時光在它身上沉淀出斑駁的綠銹,但銅戈的形式、銘文體例、字體結(jié)構(gòu)無不昭示著不凡的出身。青銅戈由秦中央督造,而那銘文中的紀(jì)年——“十四年”,宛如一聲沉重的歷史鼓點(diǎn),敲定在秦始皇十四年(公元前233年)。在那個風(fēng)云激蕩的時代,它是征伐的親歷者,2000多年后的今天,它所銘記的,正是華夏歷史的關(guān)鍵篇章——秦統(tǒng)一嶺南之役。
公元前221年,在蕩平六國平定中原后,秦始皇便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匈奴和嶺南的百越。于是,在公元前219年,秦始皇決定發(fā)兵嶺南,一統(tǒng)百越。秦軍在主帥屠睢的帶領(lǐng)下,50萬大軍兵分五路進(jìn)攻嶺南,而當(dāng)時的副帥則是一個年僅21歲的青年,名叫趙佗。
但戰(zhàn)爭進(jìn)行得并不順利,南方的深山密林里潮濕而又酷熱,加上補(bǔ)給不暢,戰(zhàn)況異常艱難,主帥屠睢也不幸戰(zhàn)死。為了解決秦軍的糧草、裝備等供給問題,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。公元前214年,靈渠鑿成。同年,秦始皇任命任囂為新任主將,與趙佗繼續(xù)進(jìn)攻廣西地區(qū)的西甌、駱越各部落,最終完成了平定嶺南的大業(yè)。這是嶺南首次完整納入中央王朝版圖,秦始皇在嶺南地區(qū)設(shè)立桂林、象、南海三郡,以番禺(今廣州)為南海郡治,委任任囂為南海郡尉,趙佗為龍川縣令,三郡皆受任囂節(jié)制。
然而秦末風(fēng)云突變,公元前209年,秦二世的暴政催發(fā)了陳勝、吳廣為首的農(nóng)民起義,六國后裔也乘勢而起。面對中原混亂的時局,任囂提出立國以隔絕中原戰(zhàn)火,然其未及實(shí)施便病重垂危。臨終之際,任囂緊急召見心腹龍川令趙佗,委以代理南海郡尉之職。任囂病逝后,趙佗一方面“絕道”“閉關(guān)”,毀棄秦朝修筑的南北通道,斷絕與嶺北聯(lián)系;另一方面,“擊并桂林、象郡”,重新整合秦置嶺南三郡,基本統(tǒng)一嶺南。
公元前204年,趙佗定都番禺,建立幅員千里的南越國,自稱“南越武王”,為存續(xù)95年的南越國奠定了基石。
和輯百越——南越歸漢
南越國建立伊始,當(dāng)時的嶺南生產(chǎn)力水平極其低下,推動當(dāng)?shù)匕l(fā)展便成為了趙佗的首要任務(wù)。但趙佗深知,振興嶺南之基在于民族融合,遂推行“和輯百越”的民族政策——首先是讓越人參政,任用當(dāng)?shù)赜型脑饺耸最I(lǐng)。其次是遵從當(dāng)?shù)亓?xí)俗。趙佗宣稱自己是“蠻夷大氏老”,“棄冠冕而著越服”,剪發(fā)結(jié)髻。在趙佗的帶領(lǐng)下,其他南下的中原漢族官吏也紛紛接受了越族的風(fēng)俗習(xí)慣。同時,鼓勵漢越通婚。最后是讓越人“自治”,此舉有效促進(jìn)了漢越融合,同時百越文化與漢、楚、秦乃至周邊文化交融共生,最終在中華文明宏圖中孕育出獨(dú)具特色的嶺南文化支系。這種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會生態(tài),是涵養(yǎng)嶺南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礎(chǔ),這對后世乃至近現(xiàn)代嶺南社會的發(fā)展,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。
而南越國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文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“同制京師”,積極仿效秦漢之制,同時也保留了一定的地域特色。
1995年,沉睡2000多年的南越王宮重見天日——這是中國迄今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年代最早的宮苑實(shí)例。其都城遺址(位于今廣州越秀區(qū)中山路一帶)面積約為15萬平方米,主體可分為宮殿區(qū)和宮苑區(qū)。考古發(fā)掘于此出土大量“萬歲”文字的瓦當(dāng)以及戳印“華音宮”“未央”的陶罐殘片。在此之前,南越文王墓還出土了戳印“長樂宮器”字樣的陶器。這些發(fā)現(xiàn)清晰地印證了《漢書·諸侯王表序》的記載——“籓國大者夸州兼郡,連城數(shù)十,宮室百官,同制京師”,實(shí)證了南越國效仿中原王朝進(jìn)行宮室營建和命名。
其中“華音宮”陶片尤為引人注目,此宮名未見于史籍記載,應(yīng)是南越國自主設(shè)置。其宮殿名或與陸賈出使南越、修復(fù)漢越關(guān)系、為南越王趙佗帶來“華夏之音”有關(guān)。通過這些宮殿銘文,不難看出南越王對中原禮制的效仿和對故土的思念,雖然稱王南越,但趙佗從未自絕于中華。
漢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196年),劉邦派遣著名辯士陸賈到番禺,游說趙佗歸附漢朝。《史記》中的《南越列傳》和《陸賈列傳》對趙佗受封有著基本一致的生動描寫。起初趙佗對漢使十分無禮,陸賈便細(xì)數(shù)趙佗的中原出身,結(jié)合楚漢之爭的歷史,指出南越和漢朝實(shí)力上的強(qiáng)弱懸殊,曉以情理,迫使趙佗改顏謝罪,最后趙佗接受漢朝授予的王印,對漢稱臣,并留陸賈在廣州“與飲數(shù)月”。
但呂后掌權(quán)后,漢越關(guān)系卻風(fēng)云突變,呂后聽信讒言,實(shí)施“別異蠻夷,隔絕器物”政策,下令斷絕與南越國等“蠻夷”之地的商貿(mào)往來,嚴(yán)禁鐵器與雌畜輸出。此舉讓趙佗頗受打擊,“恨長沙王圖己”,決計(jì)發(fā)兵攻打長沙。戰(zhàn)事持續(xù)了一年多,直至公元前179年漢文帝即位,改行安撫之策,遣陸賈再為特使,攜親筆書信與厚禮出使南越。最終,趙佗在漢廷承認(rèn)其“服嶺以南,王自治之”的前提下,取消帝號,再度歸附漢朝。在致漢文帝的回信中,趙佗解釋此前“敢妄竊帝號”不過是“聊以自娛”。他明確表示愿重修舊好,“長為藩臣,奉貢職”,并獻(xiàn)上大量南越珍寶。
在趙佗執(zhí)政的60多年里,他銳意經(jīng)營嶺南,大力引入中原農(nóng)耕技術(shù)、傳播漢字禮儀,將文明火種播撒珠江流域,推動嶺南迅速從刀耕火種的氏族社會邁入農(nóng)耕文明時代。他對嶺南文化奠基并成形及促進(jìn)國家統(tǒng)一作出了重大貢獻(xiàn),因此被后世尊為“嶺南人文始祖”。公元前137年,享壽百余年的趙佗溘然長逝。